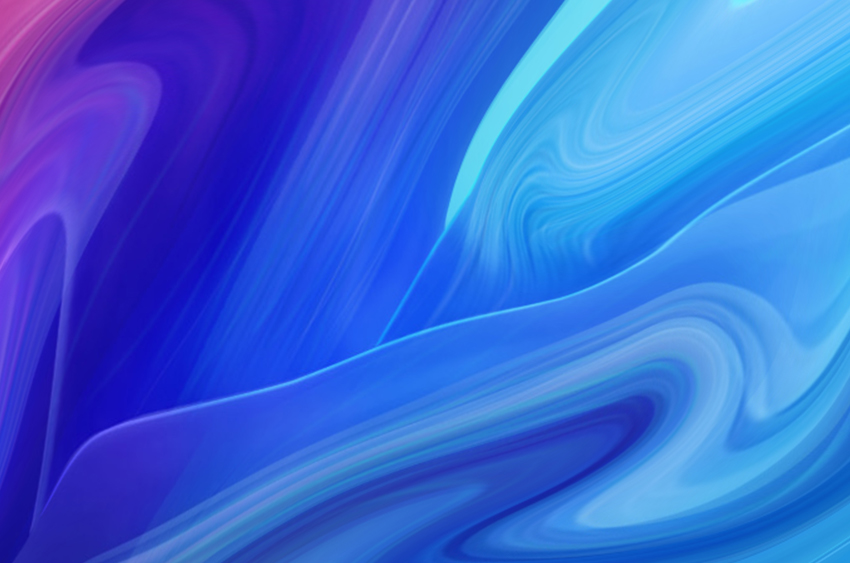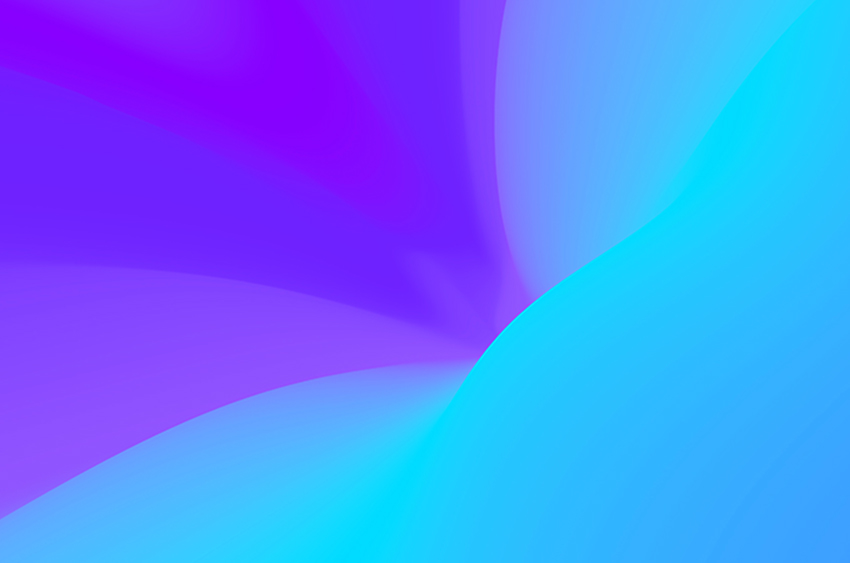既非继续违法亦非连续违法?——刑法视角下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罪数形态问题
龙非
题记:证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既非继续违法行为亦非连续违法行为,而是更接近于刑法理论中的“集合犯”的特征,即行为基于反复实施同种危害行为的犯罪意志,反复实施同类,该反复实施的行为以实质一罪论处的犯罪形态。这一认定标准与当前刑事司法程序中的处理思路较为接近,连续违法的界定本身存在诸如行为延续性要求难以满足,或者公司责任与高管责任脱节等适用问题,有必要予以调整。相关刑事司法文件中关于将信披犯罪界定为继续犯的标准,则无论在理论和实务上均存在缺陷,不值得推荐。
问题的提出
在证券行政处罚案件中,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追责时效问题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被认为是继续违法行为,即使每一次虚假披露单独构成一个违法行为,但在未被揭露之前构成违法行为的继续状态。直到2013年陈某诉中国证监会案中,案涉虚假披露年报涉及1999年报至2004年中报,法院认为实施上述行为之目的,均是为了掩盖上市公司的不良经营业绩,上述行为具有连续性,追责时效应从其行为终了开始计算,至此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又开始被界定为连续违法行为,即将多个虚假披露行为处断为一个行为,并以最后一次虚假披露行为计算追责行为。按照连续违法认定的思路在证监会第一批指导性案例的1号案中予以了明确,该案财务造假涉及2016~2019年度,证监会认为“对于跨法的连续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可秉持同样做法,即在分别评价的基础上适用新法一并处罚,并将部分违法行为发生在旧法时期作为整体量罚的酌定因素。”
在违规信披的刑事案件中,首先,实践中几乎不会将每一次违规信披行为作为单一犯罪行为予以评价,而是将历年的财务造假行为认定为一罪,这几乎是司法实践的通例。不过,关于违规信披罪究竟是继续犯还是连续犯,标准则似乎存在争议。去年最高检《关于办理财务造假犯罪案件有关问题的解答》中指出,“公司、企业违规不披露重要信息,违法行为有继续状态的,继续状态结束之日为行为终了之日,追诉期限从该日起计算。”这一表述显然倾向于将违规信披罪界定为继续犯,但上述规定与司法实践相去甚远。
一方面,司法实践中几乎并不采取继续犯的认定标准,比如在黄某违规信披罪案中,法院就认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之前,依照刑法‘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其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另一方面,司法机关也并不严格以刑事追诉标准作为限制,只要有一个年度的信披行为情节达到追刑标准,则尚不达追刑标准的其他年度仍可作为犯罪事实的一部分在量刑中予以整体考量。而这一思路显然又与严格的连续犯并不相同,因为连续犯的前提应当是每一个非法行为单独均可满足犯罪行为的构成要件。
其实,无论将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认定继续犯还是连续犯均存在缺陷:
第一,如果将每个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认定为继续违法行为,则一方面每次的虚假披露均是独立的违法行为,应当对每次披露行为单独评价并最终数事并罚,从当事人角度无疑会出现处罚畸重的情况。而且,随着针对证券违法犯罪行为打击力度的加大,法律责任的相关规定也在日趋严厉。在违法行为被认定处于继续状态的情况下,当事人基于陈年旧案而承担更重的法律责任也存在合理性问题。从证券监管部门角度也会面临多年的历史陈案也不得不追查的执法负担,而很多信息披露行为在经过多年市场沉淀后其实已经并无追查的必要性,因此认定为继续违法对当事人和执法机关而言均显得不合理。
第二,如果认定为连续违法行为,又面临不同年份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内容未必均具有延续性,典型的如重大事项未披露,就未必能够与后续完全无关的财务造假构成连续违法的概括故意。不仅如此,由于连续违法在法理上并非实质的一事而只是处断的一事,因此对于每次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涉及的董监高,就可能因为后续离职等原因而无法与公司最后一次实施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共享”追责时效的计算时点,进而导致对于之前年份的违法行为,在极端情况下可能出现只有公司法人担责而无董监高个人承担责任的“公司虚拟担责”现象。
分析
出现上述争议的主要原因在于,信息披露违法与一般的单一违法行为存在显著的差异,特别是财务造假的虚假信息披露明显具有持续性,但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又具有阶段性,与典型的继续违法行为不同,而不同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之间,虚假披露的信息内容并不一定具有延续性,这又与典型的连续违法行为有所区分。
其实,在大陆法系法域中,证券虚假陈述行为通常会被认定为“集合犯”,即将多年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认定为一个违法行为,最终一次的虚假披露行为作为行为的终了时点开始计算追责时效和新旧法适用。比如在台湾地区“高等法院” 2021年度金上重诉字第2号“刑事判决”中就认为,“……犯罪之实行,学理上有接续犯、继续犯、集合犯、吸收犯、结合犯、连续犯、牵连犯、想象竞合犯等分类,前五种为实质上一罪,后三者属裁判上一罪,因实质上一罪仅给予一行为一罪之刑罚评价,故其行为之时间认定,当自着手之初,持续至行为终了,并延伸至结果发生为止,倘上揭犯罪时间适逢法律修正,跨越新、旧法,而其中部分作为,或结果发生,已在新法施行之后,应即适用新规定,不生依‘刑法’第2条比较新、旧法而为有利适用之问题……查本件被告林正清等人之行为时间均持续至2007年,均在2006年7月1日生效施行之刑法修正之后,故本件除没收应径行适用新法外,其余部分尚无刑法新旧法比较适用之问题。”
虽然集合犯与连续犯相似,但二者存在实质差别。所谓集合犯,是指在构成要件上本即预设有反复实施同种行为的一种犯罪形态,最早是由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提出。李斯特认为,常见的集合犯形态包括常业犯,即将某种犯罪行为作为一种职业谋生手段,比如赌博罪中“以赌博为业”即为一例;又或者营业犯,即从事某种非法经营行为,如非法经营罪。还有则如常习犯,即犯罪行为的反复实施本来就是其固有特征,而往往以行为次数、累计数额等作为量刑情形,比如走私罪、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许多罪名也具有类似的特征,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即属其中之一。
在刑法学理论中,由于连续犯是处断的一罪,实质的数罪,因此其追诉时效的计算时点需要专门予以规定,而集合犯则是实质的一罪,其追诉时效无需法律特别规定,依其固有特征当然应当以最终一次犯罪行为的完成作为整个犯罪终了的起算时点。而且集合犯并不要求多个行为之间如连续犯那样具有严格的延续性,多个行为的具体内容可以有所差异,但实质上均是基于同一个犯罪意志而实施即可,从而可以将不完全具有延续关系的多个信息披露行为置于一个犯罪行为中予以评价。在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中,也就不再需要特别分析不同年度之间的财务造假是否具有延续性的问题。
由此反观刑事司法机关的实务操作,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则更接近于“集合犯”的认定标准,即将历年的信披行为作为一个整体,以最后一次信披作为行为终了日,不以继续状态评价,但历年的信披行为只要有一个年度构成犯罪,其他年度即使不达追刑标准,亦作为一个整体在量刑中予以考量。
如果在行政处罚领域也引入集合犯的概念,不仅解决了当前刑事追责与行政追责认定标准明显不一致的问题,还可以解决类似“公司虚拟担责”的执法困扰。由于集合犯本质上是实质的一罪,整个过程仅被视作单一犯罪行为的不同实施阶段而已,因此对于在过往年份中负有责任的董监高,即使在此过程中离职也不会影响追责时效的计算,只是在应担责的具体事项范围时有所限定而已。
结论
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在性质上更接近于刑法理论中的集合犯概念,而这也基本符合当前刑事司法程序中的认定思路,这一认定标准有必要明确并加以统一,行政处罚领域的连续违法认定虽然与之接近,但仍有实质差异,而继续犯的认定思路则较在理论和实务上均存在较明显的缺陷。